DPS 周刊 206 - 闪回厦门

前阵子在厦门玩了几天,随手记录一下。
第一顿饭是上青本港海鲜,这家上了点评的黑珍珠榜。打电话过问能不能订位,答曰订位只有限定菜单,而且低消400。不订位可以在大堂吃,但可能需要排队。
反正住在边上,就走过去,刚好开店。其实订位吃的是 fine dining,大堂吃的都是自己在鱼缸前点菜。那当然跟着本地人在鱼缸前面点:
- 一例小份卤鹅 (服务员劝说两个人小份就够了)
- 凉拌海蜇(分量非常大)
- 红蟳蒸米糕(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满膏,下面的米糕类似于煲仔饭,但没有锅巴)
- 蛏子(尽管从小吃到大,第一次见到这么饱满的)
- 煎斑节虾(摆盘很有意思,两只虾正好是颗爱心)
- 炒地瓜叶(也是听服务员推荐点的)
海鲜非常新鲜,服务员也很克制,劝我们不要多点。最后买单405,感觉非常实惠。
第二天早上找到一家叫 Blues 的独立咖啡馆,有深浅两种 SOE 的豆子,请他们用深烘 SOE 做了一杯 dirty,浅烘 SOE 做了一杯美式。还不错,喝完还带了一包深烘的豆子回去。

然后赶去中山路八市一带转。到八市附近堵得不行,遂下车步行。兜兜转转,看到一家老字号的沙茶面,想看看和东南亚的有啥不同。
点了最简单的一份,18元,就是罗汉肉 + 豆腐 + 鱼丸。汤汁里面没有加椰浆,好像加了花生,没有东南亚的那么浓郁,恐怕这是最大的不同。查了下,罗汉肉应该是猪的横膈膜,瘦肉和筋膜分层,非常有嚼劲。鱼丸里面还嵌了猪肉,不像东南亚是纯鱼肉。

吃完走了两步,碰到一家卖水果的。有不少现切的,可以混拼,随便选了一些平常不怎么吃的,淋上酸梅汁,非常解腻。一大盒26元。
走到海边上的星巴克,占了四层,正好可以看到对面的鼓浪屿。于是跑进去点了一杯云南手冲,豆子还不错。
出来走回中山路,正好碰到黄则和,厦门的老字号,于是走进去点了厦门海鲜面,牡蛎煎和冰镇花生汤。
厦门海鲜面和东南亚流行的福建虾面很相似,看来福建虾面还是能找到源头的。牡蛎煎是现做的,一锅大概能出十份,等一锅大概五六分钟。硕大的牡蛎煎完之后,只剩小小一颗,倒是地瓜粉煎熟之后变成胶质,口感独特。冰镇花生汤加了西米露,和热的花生汤完全不一样,个人还是偏爱热的多一点。

第三天中午听当地朋友的推荐,要么宴遇,要么闽和南。跑去一看,两家贴在一起,看了下菜单,还是选了闽和南。
- 脆肚海鱼羹(除了鱼丸,猪肚,还有肉丸,都非常有质感)
- 小章鱼(上次在厦门街头吃这个,感觉像在嚼橡皮,这次体验不错,一是章鱼很嫩,没有很大味道,二是料汁很独特,酸里带辣,一下子把味道带起来了)
- 土笋冻(和上面一道一样,料汁比街头的更有特色。没有料汁真吃不下去)
- 姜母鸭(这道做得一般,鸭肉没有完全入味,可能还是街边的铺子做得好。优点是不太腻,可以全部吃完)
- 炒油麦菜(也是听服务员推荐的)
- 侨乡蒜蓉包 + 热花生汤(包子皮非常软嫩,有点像麻薯的质感,可能是用地瓜粉做的?热的花生汤果然好吃,这家的火候不错,花生炖酥了,但还没有散)
最后结账,360,也很实惠。




我们已经开通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如果你想及时读到 DPS 的全文,不妨直接付费订阅:
关于支付的详情介绍,可以访问这一页面。
Recap
Fred Rivett 认为:我们一层一层地构建自己,而最先奠下的那些深埋的层面,往往是我们最没有选择权的。
- 旧的信念会剥落,新的信念会取而代之。后来的层次有时能渗透得更深,一些新近的信念甚至能成为基石。
- 每一个小小的胜利都强化了前一个,使我逐渐远离过去的自己。
- 当认知失调站在你这边时,它是美妙的。只要健康的自我认知与行动不一致,它就会冒出来。
- 改变信念并不容易——无论是关于外部世界,还是关于内心世界的。
- 你的行动会追随你的自我信念。

Edwin Chen 曾在 Twitter、Google 和 Facebook 任职,摒弃了传统风投,七年前离开硅谷,选择用自己在大科技公司十年积蓄的几百万美元为 Surge 提供资金。
- 陈雇佣了一支超过一百万人的零工团队,来自五十多个国家,负责设计可能难倒 AI 的问题、评估模型的回答,并编写标准来帮助 AI 生成更完美的答案。
- 他指出,Surge 只有 250 名员工(包含全职、兼职和顾问),而其主要竞争对手 Scale AI 的员工人数是其四倍,但营收更低。
- 据陈介绍,公司几乎从第一天起就盈利,目前估值约为 240 亿美元。
- Turing 的 CEO Jonathan Siddharth 表示:“数据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算力和能源一样。我认为企业在数据上的支出占算力支出的 10%-20% 是合理的。”
- 一些老牌企业(如澳大利亚的 Appen)也在重新定位,专注于生成式 AI,并向中国的模型厂商提供服务。

Robin Guo 认为生活更像是德扑,而不是国际象棋:
- 在德扑里,你即使打得完美也可能输,而有的人胡乱出牌却能把整桌人都赢光。
- 国际象棋假设了一个受控环境:信息完全透明,只有一个对手,结果可预测。
- 生活要混乱得多。它有多个玩家、隐藏的底牌、随时可能改变的规则,以及足以击垮技巧的运气。
- 一旦你开始用扑克的视角看待生活,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其实在一个扑克的世界里用下象棋的思维在行动。难怪他们常常因“正确”的行动没有回报而沮丧。
- 扑克带来的最重要教训是:要以概率而非结果来思考。

Gabe Rivera 在20年前创立了 Techmeme:
- Techmeme 是科技创始人、管理者、投资人、创新者、写作者以及各类意见领袖必看的新闻网站。
- 它通过唯一可能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作为一个_聚合器_,链接到关于科技重大事件的最佳报道,对它们进行排序,并融合最值得关注的社交媒体帖子与其他内容。
- 与 RSS 阅读器不同,Techmeme 并不是让你自定义的工具。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个 Techmeme。
- 尽管科技、互联网和新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Techmeme 却保持了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 虽然 2005 年的博客形态已经式微,但博主们和潜在的博主们依然在发表内容,只不过是在社交媒体、新闻简报,或者传统新闻媒体网站上的“博客”栏目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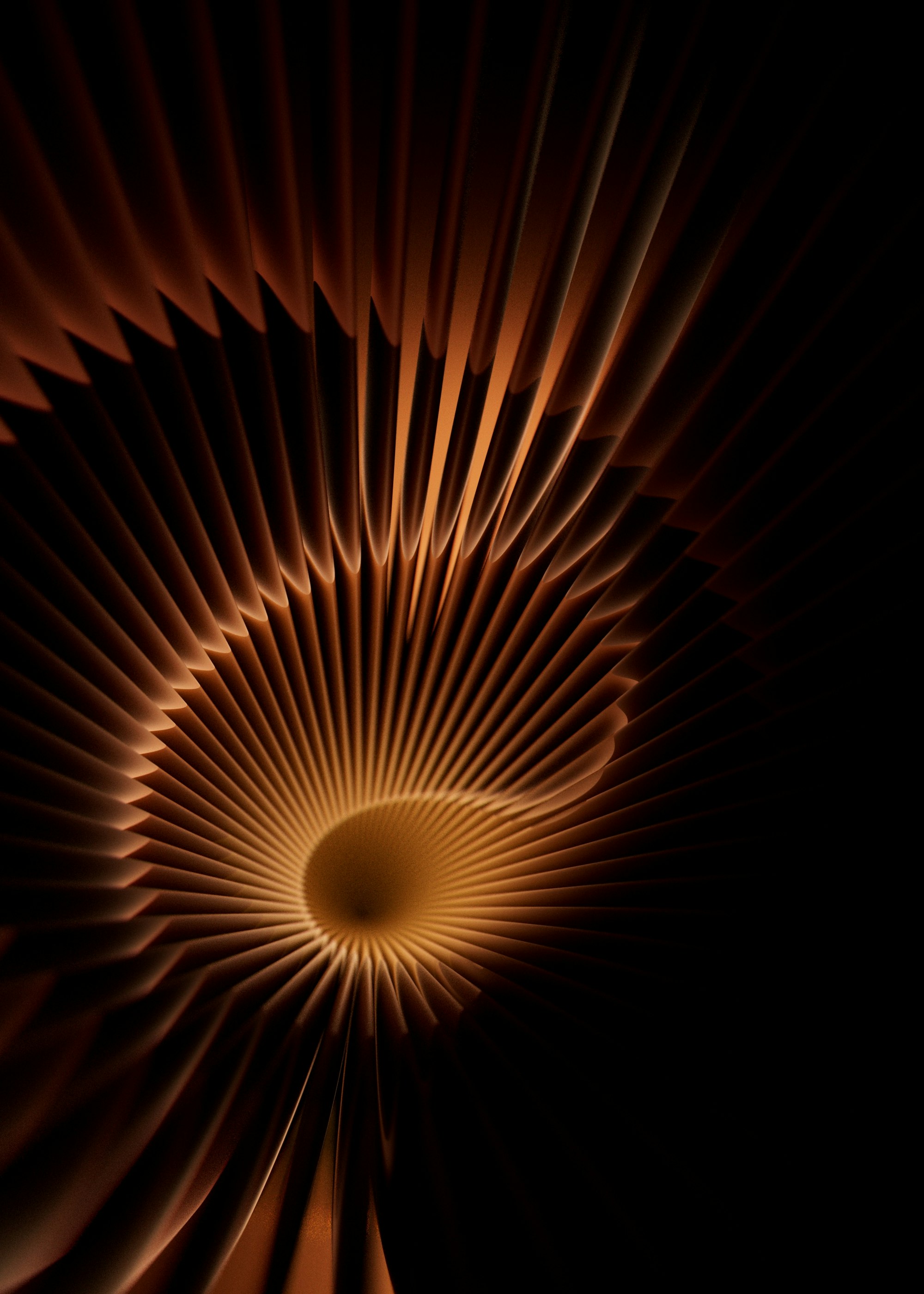
Scott Werner 建议我们要滑向冰球将要到达的位置,而不是它曾经在的位置:
- 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预测了冰球的走向,而是因为他能滑到冰场上的任何位置,并保持随时接球的状态。预测只是滑行之后的附带结果。
- 你不会被 AI 取代。这种担心方向错了。你会被那些在你还在争论冰面是否真实时,就已经学会滑冰的人取代。
- 找到一家真正理解这一点的公司很重要。它会愿意花钱让你更快。它明白我们已经不再是在打传统的冰球赛。
- 冰球不会在乎你的经验。当你还在读这句话时,它已经从你身边飞驰而过。

Sean Goedecke 建议在设计软件系统时,做最简单而有效的事:
- 把时间花在深入理解当前系统上,然后做最简单有效的事。
- 然而,和许多技能一样,真正的掌握往往在于学会何时少做,而不是多做。
- 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应用: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然后只在新的需求迫使你时才去扩展。
- 当你在看一个问题时,最先想到的几个解决方案往往不是最简单的。
- 找出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需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做法。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的工程。

姚雨顺认为 AI 的下半场已经到来 - 将从解决问题转向定义问题。在这个新时代里,评估比训练更为重要。
- 现在突然发生了什么不同?用三个词来概括:强化学习(RL)终于奏效了。更准确地说:RL 终于能够泛化了。
- 要在这一阶段中茁壮成长,我们需要及时转变心态与技能,更接近于产品经理的思维方式。
- 在 AI 的前半程,方法比任务更难、更令人兴奋。
- 方法往往比单个任务更通用、适用范围更广,这使它们尤为有价值。
- 一种出色的新方法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基准上持续爬坡,因为它足够简单和通用,其影响往往超越单个任务。

Simon Willison 认为终于可以给 agent (大语言模型代理)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了:
- agent 代理会在循环中运行工具以达成目标。
- 术语只有在你能够确定听的人对其定义一致时才有用。
- “循环中运行工具”这个模型内置了一种基本的记忆形式:那些工具调用是作为与模型的对话的一部分构建的,而对话中的前一步骤为实现当前指定目标提供了必要的短期记忆。
- 因为有一个关键特性仍然是人类员工独有的:可问责性。人类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从错误中学习。
- 有趣的是,人类也拥有自主性(agency)。他们能形成自己的目标与意图,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自主行动——同时为这些决策承担责任。

Joan Westenberg 认为物理上的整洁并不总能解决心理上的烦躁:
- 早晨第一件事整理床铺可能会变成同样的逃避,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分心行为,看起来很有美德,但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没有任何改变。
- 下次醒来时,克制去碰被子的冲动。坐下来。直面自己的内心。
- 问自己:这个仪式让我专注当下,还是让我表演?如果答案是表演,就让床单保持凌乱,直到你完成真正的工作。
- 我们把生产力技巧和晨间习惯奉为神圣。但丑陋的真相是,如果这些仪式建立在未经审视的杂乱之上,它们什么意义也没有。
- 先清理头脑。让床铺等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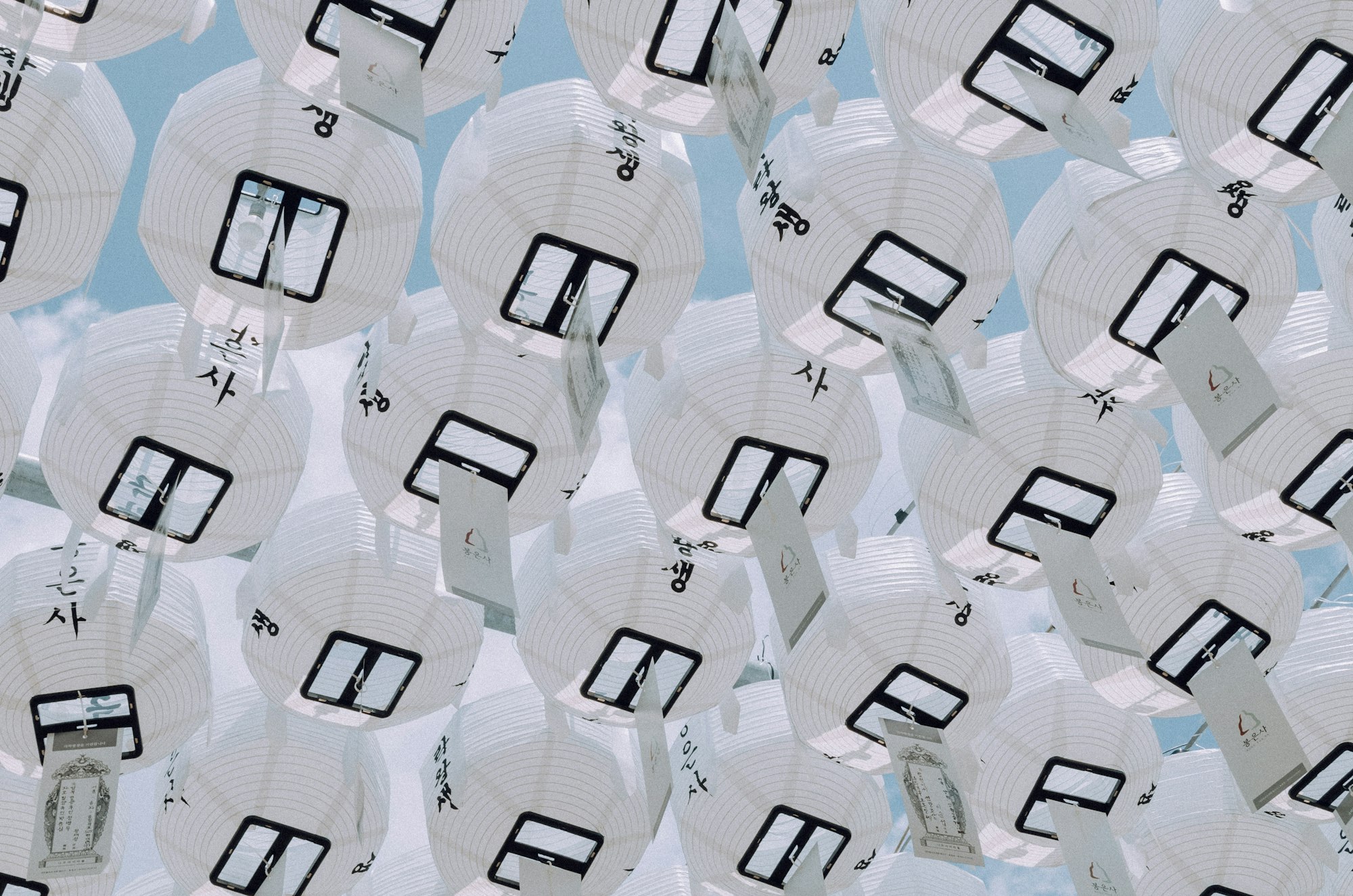
Josh Swords 认为探索就是尝试新事物;开发就是坚持已验证有效的做法:
- 优秀的学习者会先大量探索,等他们了解更多后,才能放心地去开发。如果跳过探索阶段,就会陷入困境。
- AI 消除了挣扎。但挣扎才是关键。那才是你学会思考的方式。
- AI 本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探索,但它常常被用在过早的开发上。
- 这就是所谓的“开发陷阱”。你得到了一个答案,但代价是失去了寻找答案(甚至更好答案)所需的技能。
- 正确的平衡更像强化学习(RL)中的代理:先探索,再开发。

Joan Westenberg 认为我们积累的工具越多——应用、设备、平台、AI 助手——就越觉得自己能力丰富。但矛盾的是,每增加一层,我们似乎就变得更脆弱。
- 问题不是你不能重新学习这些东西——你可以。而是你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 纸面上,你是一个拥有十二套系统的生产力强者。实际上,一旦拿走这些应用,你就无所适从。
- 无害的外包和危险的依赖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我们能感觉到自己何时越界。
- 你不是因为有趣才去做。你是为了证明自己依然能做。
- 罗马的衰落,被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体系所缓冲,直到它们不再坚不可摧。如果我们的衰落到来,也会被应用所缓冲。
- 我所知道的是,个人能动性就像货币,如果不断膨胀却没有储备,它的价值就会丧失。而如果你想要的是主权而不是依赖,你就必须捍卫它。

Scott Jenson 认为大语言模型事实上已经“黑入”了我们的社会协议,让人们误以为它们比实际更聪明:
- 他的职业生涯给了她两条应对不确定性的教训:第一,技术总是往下流动;第二,我们通常一开始走的都是错路。
- 早期工厂依赖河流获取水力,但发电机的出现让工厂摆脱了地理限制。
- 最初,工厂只有一个大型发电机,需要复杂的滑轮系统把动力传递到整栋建筑,这使得生产流程非常复杂。
- 随着发电机体积缩小、成本降低,工厂可以在多个位置安装发电机。这种变化比第一次更解放,因为它催生了装配线。动力开始适应生产流程,而不是流程去适应动力,从而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 他用这一历史转变来类比 1980 年代末的情况:从笨重的中央主机到小型桌面电脑,正是同样的模式——由大而集中转向小而分布。如今 LLMs 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Julian Schrittwieser 认为到 2026 年年中,模型将能够自主工作整整一天(8 个工作小时)。其实这个估算还是有些保守,刚刚发布的 Sonnet4.5 自主编程超过了30个小时:
- 早在全球大流行的时间和规模已经可以通过指数趋势推算出来的时候,政客、记者和大多数公众评论员仍然把它当作一个遥远的可能性或局部现象。
- 考虑到在许多行业中,性能改善已经连续多年呈现指数型增长,如果这些改善突然停止,将会非常令人惊讶。
- 在 2026 年结束之前,至少会有一个模型能在多个行业中达到人类专家的水平。
- 到 2027 年底,模型将在许多任务上频繁超越专家。

Claude Code 是如何炼成的?Gergely Orosz 采访了 Claude Code 的两位奠基工程师 Boris Cherny 和 Sid Bidasaria,还有产品经理 Cat Wu:
- Claude Code 的想法最初来自一个命令行工具,它用 Claude 来显示工程师在工作时听的音乐。
- Claude Code 中 90% 的代码是它自己写的!
- 团队的节奏非常快,每位工程师每天大约发布 5 次。
- 使用 AI 代理进行代码审查和测试,推动测试驱动开发(TDD)的复兴,自动化事故响应,并谨慎使用功能开关。
- 产品过剩意味着模型已经能做某件事,但运行 AI 的产品尚未构建出捕捉这种能力的方式。

强化学习之父 Rich Sutton 在2019年就揭示了算力即一切的道理:
- 从 70 年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利用算力的方法最终是最有效的,而且优势巨大。
- 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改进,研究人员往往试图利用自己对领域的人类知识,但从长期来看,唯一重要的是能否利用算力。
- 基于人类知识的方法往往会让方法复杂化,使其不适合利用那些依赖算力的一般方法。
-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搜索和学习是两类最重要的技术,用来发挥海量计算的作用。
- 另一边是更新的统计类方法,它们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HMM),需要更多计算。结果依然是统计方法战胜了基于人类知识的方法。

本周的生产力日报集合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收到最及时的推荐,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付费解锁更多增值内容,我们下期见。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直接订阅这份电子报 ⬇️


















Comments ()